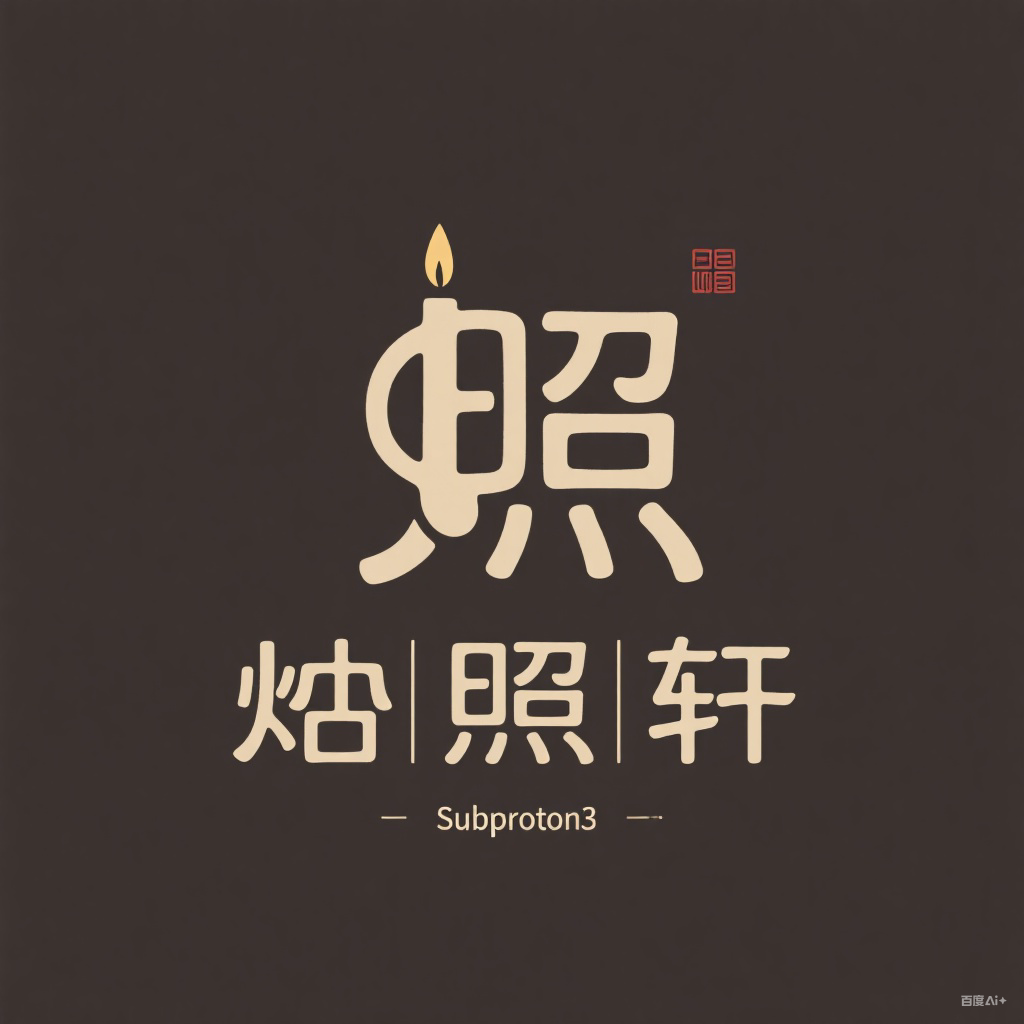#降龙#
因为欧洲并没有贯通全境的大型地表径流。
其实形成洪水的主要原理是要有一片极为广阔的被饱含水分的季候风吹拂的山脉地区。
这些风沿着山脉爬坡,就会在一定海拔高度上形成季节性集中降雨,接着由巨大的山谷担任收集器,将这些降雨统一收集到山谷底部的峡谷里,并最终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洪峰,扑向下游冲积平原地区。
我们的黄河、长江,本质上就是上游山脉地区收集水汽集中输出的结果。这是大型河流,因此有强烈的季节洪峰问题。
事实上孟加拉也被喜马拉雅山脉采集的季节降雨搞到年年洪灾,道理是相同的。
但是欧洲比较巧妙,

它的山脉刚好挡在海洋与平原之间,而不像我们的地形,是平原处在山脉和海洋之间。

这导致海风带来的水分还没有进入欧洲腹地就被山脉刮出主要油水又给送回大西洋和地中海了,结果就导致欧洲遍地都是中小河流,而且季节洪水相对较小,没有我们的长江黄河这样的大型河流。
进而导致欧洲也没有我们这样的降水充沛却无险可守的超大冲积平原来作为巨型统一国家的地理基础。
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何以这么成熟和发达,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季节洪水每年都给中原王朝的年度大考。
考得好,那么超大冲积平原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周围草原丛林苦寒瘴疬之地的苦哈哈们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我华夏天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考得不好,那么多年的积存一卷而空,有亿万斯民却无可支半年的口粮,那么这亿万子民就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彼此攻杀来决定谁有资格去吃仅存的余粮,而在这彼此攻杀期间,东南西北的外敌往往大有可乘之机。
其实这就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文明史的基本逻辑。王朝新立,政治清明,社会信用卓著,自然可以轻松调集人手有效组织,考好这些大考。往往就有五六十年的太平盛世。这段时间中原人口暴涨,浑身都是肌肉,自然不免要追亡逐北、封狼居胥。
然而常在路边走,哪有不湿鞋?想要无事故运行一百年以上谈何容易?往往总在百年上下,要来一次黄河改道、江淮泛滥之类的大灾。这一次王朝往往可以靠过去五十年的积存广施赈济稳住核心地区,但限于古代交通通信水平,边远地区就鞭长莫及,就要产生无食流民与尚有余粮的本地人之间的生存斗争。这个阶段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失地农民与大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这些农民名下其实有地,但地被淹没了,房产和积粮被洪水摧毁了,只能大规模的奔向周边未受灾地区就食。而一旦这些地区没有及时得到中央调来的粮食补救,两倍人吃半份粮(这些周边地区只是受灾较轻,并非没有受灾),就要发生巨大的“土客矛盾”。出现流民集团对地方团练坞堡的大战。
这一轮大混战就要耗尽王朝花了五十年积累的元气,虽然不至于直接导致王朝崩溃,往往也要发生东西周、东西汉、早晚唐、南北宋这样的由盛转衰的趋势变化。
因为这一下不只是财政和粮食安全受到重创,政府信用往往也布满了裂痕。既然如此,河工河政就必然进一步趋向废弛,而这每年一考考不过的频率会远比前半程的完美状态大大提高。
而这时候周边蛮族就会从前半程的悲惨境地获得喘息之机,并在劫后余生之中产生数十年后对中原王朝造成心腹大患的杰出领袖。
其实这不是这领袖自身有多杰出,而是长江黄河通过突破防线而冥冥中预定了这些少数民族考区要出现几个保送名额。
而进入下半场后,因为长江黄河频繁突防,少数民族几乎没有再受到中原王朝的主动扫荡,休养生息数十年,就要在两河的无形策应下南下东进,直到引发改朝换代的滔天大劫。
而这整个循环里,如果能把长江黄河发作的时间尽可能推迟、频率尽可能拉长,就成了决定国祚长短的至关重要的要害。
可以这么说——如果古代就有了钢筋混凝土技术和挖掘机技术,中国周边根本不会有所谓的狄夷之地,我们将毫无悬念的吞并新疆蒙古朝鲜越南,并越过喜马拉雅山横扫整个南亚。
捆住我们手脚的,正是实在无法镇住这两条水龙足够长的时间,而每次新开局就开始倒数的那一百年十年,即使我们武威极盛、运气极好,也最多只能及于西至哈萨克斯坦,南至交趾吐蕃、北至朝鲜的极限。到了这时,水龙一翻身,我们就要转向内缩了。其实真正打败我们的,一直就不是周围那些文化不发达、甚至军事都很落后的蛮族,而是我们家里锁不住、压不服的两尊龙神。
“防汛”听上去是非常无聊、平淡的两个字,但却是我们每年最紧要、最致命、最凶险的大战。我们和龙族打了两千多年,直到最近这一百年,才真正的用钢筋混凝土把这些龙族镇压在了现在的河道里。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它们能量的源头——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实施大型水利工程、在平原地区广泛建设海绵城市,要分流、管理这源头的“漏斗”的汇聚效应,从根上剥离龙族的神力源泉。
到我们可以决定每年每月有多少血液流进龙神的血管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就永远的终结了过去三千年最关键的轮回诅咒。
这之后的一切,都史无前例。
这就是“年年防汛”四个字背后的东西。
转载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2387644/answer/4124905196